文|阮义忠
人对往事的记忆就像锁在不同抽屉里、舍不得丢的杂物,有些经过归档,有些无法分类,就那么一起掺杂地搁着,随着岁月的堆垒而尘封。某日不经意地打开一个抽屉,那被忘了、如同隔世般的旧事便猛然回魂,又有了温度、呼吸和生命,过去与现在又接续上了。
我的家乡头城是个东台湾靠海的封闭村子,居民一半务农、一半打鱼,连镇上那家历史悠久、破破旧旧的戏院,也有个恰如其分的名字——“农渔之家”。这家戏院是无数镇民的精神家园,也是我童年时的梦想窗口。陪祖母在这儿看的一出出歌仔戏,让我对中国古代英雄或奸臣的舞台形象深信不疑,直到后来上了历史课,印象也很难纠正。

电影盛行后,歌仔戏跟着没落,戏院上映的多半是日本片,宫本武藏、盲剑客是大家心目中的偶像,小林旭、石原裕次郎在黑社会电影中的穿着打扮,乃至于一举一动都是年轻人效法的对象。在本土电影方面,大受欢迎的则是模仿美国《劳莱与哈台》的喜剧片《王哥柳哥游台湾》。在交通不便的60年代,岛民们透过电影,仿佛也游遍了台湾的名胜古迹。
胖得像酿酒桶的王哥是擦鞋匠,瘦得像电线杆的柳哥是三轮车夫。王哥中了爱国奖券,邀好友柳哥环岛旅行。两个土包子在旅途中糗事不断,既谄媚别人,又挖苦自己。情节虽然在戏谑中也有温情,却老让我觉得台湾人的命运实在坎坷。
在那个年代,我们对中国大陆的点点滴滴与日本的形形色色,比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土地清楚多了。台湾被日本侵占了半个世纪,“皇民化”的影响早已深烙人心,而对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而言,“中华民国”只是暂时落难至此,迟早要回家去。像陕西路、青岛路、南京路、长安路、西藏路、沈阳路、迪化街、宁波街、哈尔滨街……这样的大陆省名全台湾可见,提醒百姓“毋忘祖国”。城里、郊外布满“反共抗俄”、“保密防谍,人人有责”、“匪谍就在你身边”等标语,仿佛字写得愈大、愈漂亮,“反攻”大陆就愈有可能成功。
此外,桥头、巷弄、山顶或海边,不时会出现“此处禁止测量、描绘、摄影、狩猎”的警语,仿佛无处不是禁区。海岸线更是禁区中的禁区,相隔没多远就有海防部队的岗哨,既防走私偷渡,又防想家的人投奔对岸。在那期间,小小的台湾实际上是个大大的隔离岛,因为“政府”把自己的人民给关起来了,直到蒋经国“总统”于1986年制定解严政策。
还好,有部分海岸线在当时是解禁的,那就是全省为数不多的海水浴场。在这里,浪花声与人民的欢笑仍能齐鸣。我就是一个幸运者,家离海水浴场只有二十分钟路程。尽管父母三令五申,禁止小孩在没有大人陪伴的情况下去玩水,我们却时常偷偷地到那烫得可以焖蛋的沙滩上打滚儿,再冲向冰得刺人的大海中,几个钟头一下就过去了。回家前怕自己看起来太干净,就用菜园里的泥土往身上抹,好让妈妈以为我们是在泥地里撒野。
阮义忠摄影作品
我们呼吸的空气常带着海味,发丝里不时夹着海沙,胳肢窝里总是沾有盐巴,可是大部分人却不敢梦想有一天会出海远行。我的二哥就像一些不甘被土地绑住的农家子弟一样,一直梦想当船员,幻想周游世界。
那时,乡镇村落的电线杆还都不是水泥做的,一棵棵树干被削得圆滚滚的,浸过黑黑的柏油后,便孤零零地立在道路两旁。人们在上面张贴宣传单或寻人启事,其中经常出现的就是征召船员的广告。
二哥每隔一阵子就会央求父亲让他上船去试试,央求过几年后,终于明白这件事是无望的。后来,我们家七兄弟之中,唯一留在老家当木匠的就是他。当初最想出走的,却认命地成了唯一继承祖业的人。事实上,我知道他好几次都有离家出走的念头,也不止一次地在深夜里听到他蒙着被子叹息、饮泣。
跟他一样,在成长的过程中,我也一直深怕被钉牢在这个沉睡已久的小镇里。自古以来,镇上的每个人都过着跟父母一样的生活,仿佛命运老早就被决定了,时代的脚步、社会的变迁都跟我们无关。从小到大,或许就是靠着喜欢观察、创作的天性,才让我能享有一方自己的天地。
还没分家之前,我们和四叔、五叔在同一个屋檐下过日子。每房有一间卧室,三个媳妇除了侍奉祖母外,还轮月掌厨,负责喂饱三个家庭二三十口人的肚子,家事虽然粗重,彼此倒也和乐融融。我们三房的寝室在炉灶、餐厅的楼上,四叔、五叔两家则是住在隔个过道的木料仓库二楼。
阮义忠摄影作品

像那时大多数的人家一样,四叔、五叔都受过日本教育,在镇公所上班,其中一位还当上课长,算是镇上的小资阶层。在那不经申请就不得聚众的年代,民间的交谊活动都得偷偷举行。四叔、五叔的房间隔着一个宽大的空间,时常被他们用来举行舞会。四叔会吹萨克斯风,他的一些朋友会打鼓、吹小喇叭以及弹低音贝斯,一个三五人的小型西乐队就这么组成了。长大之后回想起来,那不就是爵士、蓝调吗?想不到头城也能如此赶时髦。原来,平淡无奇的庶民生活背后,也总有意外暗自运作着。
我们从小就在封闭的环境中成长,而那一场场的秘密舞会,就是一窥大都会时尚的时机。若是碰到有人密报,警察上门取缔、舞客四处逃窜的情景,也能让我们看得心跳加快,真是兴奋又刺激。每次有舞会,保守的父母都会禁止我们接近。我当然没那么听话,等父母睡着后,便去趴在窗口看跳舞。看久了便能去帮忙摇留声机,运气好的时候还能上场摇沙铃。
白天严肃木讷的长辈,在晚上仿佛变了个人似的,活泼、可亲又有趣。可保守的父亲却绝不可能如此,他在白天与晚上都是一个样子,严厉又寡言,永远在现实世界中扮演着一成不变的角色,从来不提过去。这样的印象一直维持到我高中时的某一天,在整理杂物时打开家中一个老橱柜。
阮义忠摄影作品
那时四叔、五叔已跟我们分家,五婶到小学教书,四婶则是在镇上开了一家杂货店,两家的经济情况都愈来愈好。家人懒得整理他们原来的房间,我便把它打通、改造,变成由我一人独享的空间。四叔留下一个还不错的二声道音响,让我接近了巴赫、莫扎特、贝多芬、舒伯特……我用家里的剩木料做些摆设、装置,再把五叔留下的书桌椅摆在恰当的位置,将辛苦收集的世界文学名著放上书架。高中三年,这里既是我的画室,又是我的书房,迷上古典音乐后,还在里面练过几个月的小提琴。
在整理空间时,我把一个堆满家中杂物的橱柜撬开,发现了不少家族的老东西,其中包括一面沉重而纹路细致的古铜镜、一把日本武士刀、两顶降落伞、一顶日军钢盔,以及为数不少的日文杂志、书籍。我揣摩,那面老铜镜可能是祖先从唐山到台湾时所带的传家宝,武士刀、降落伞以及钢盔则说明了家族有人曾被拉去当日本军夫。
从小我就不曾听过大人谈日据时代或是国民政府初迁来台的事,就是追问也没人理,仿佛一不小心就会惹祸上身。直到许多年后,我离开家乡到台北工作,才从一位同事的口中得知,台湾曾于1947年发生过“二·二八”事件。对当时大多数的台湾人而言,这块土地的历史就像缺了许多片的拼图,不齐不全,模棱两可。
那两顶降落伞的布料可真好啊!在那物资缺乏的年代,连办完丧事后,写满黑字的白粗布挽联都会被拿来做内衣裤,美援的面粉袋也常被改成外出的便衫。我不敢探问降落伞的来源,自己偷偷把它裁了,缝成衣裤,穿出去拉风极了。后来,我才从大哥那里知道,爸爸年轻时因为手艺好,曾被强拉去修补弹痕累累的日本零式战斗机。那时的日军已是强弩之末,国力衰弱,连修补飞机上的破洞,也只能用木料。武士刀和降落伞,也许就是爸爸不得不接受的薪饷。原来,爸爸也是有过去的人啊!
无可避免的,我们从小就经常会碰到绰号“老芋仔”的外省军人。记得海边一个小渔村的附近有个营区,大家管里面的人叫“大陈仔”。小时候以为大陈和福建、广东一样,是大陆的一个省份。长大后才知道,它是个属于浙江省台州列岛的岛屿。1955年2月,台湾当局在美国第七舰队的护航下,将岛上的一万八千多军民全部撤退到台湾。由于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来台,故被称为“大陈义胞”。
学校里的国语课多半由外省老师担任。他们各有各的腔调,发音也不标准,所以很少学生能讲字正腔圆的普通话,我就是其中之一。那些老师都非常凶,仿佛把无处宣泄的郁闷都发在小孩身上了。记得小学时,只要是作业没交或是考试不及格,就会被狠狠地处罚。那种被戒尺打在手心、屁股或腿肚上的疼痛,直到现在想起来还会害怕。长大后想起来,对他们倒有几分同情。他们仓促惶恐地来到台湾,一夕之间与亲友、所爱天人永隔,那种痛岂止是锥心!
有些老师相当有学问,或多或少都对我产生过影响。比如说,我的绘画天分最早就是被读初中时的美术老师肯定的。毕业于杭州艺专的他,为我们这些乡下小孩带来了以往所不熟悉的艺术品位。读高一时的导师则是位精通甲骨文的学者,经常讲课讲到兴起,便在黑板上画些甲骨文让我们瞧瞧。正是由他的口中,我首次知道了李济、董作宾以及许多其他的著名知识分子。
到台北工作后,我更是发现,在一个小小的小区,或是短短的一条路上,往往就汇聚着来自大陆各个不同省份的优秀人士。这些学者、专家把厚实的传统文化,较先进的工业、金融知识勤勤恳恳地传播于台湾小岛。中华文化的种子有幸不受乱世摧残,在海岛的呵护下开花、结果。
二十岁那年,我开始在海军服役三年,台湾的各式军舰,除了潜水艇之外,举凡巡洋舰、驱逐舰、运补舰、抢滩小艇,全都上上下下不知多少次。我是通讯士官,必须经常背着沉重的PR77无线通话器从大舰跳到小艇,再从小艇跳到滩头。有时还得在风浪大作的海上,从小艇爬绳梯上军舰甲板,随时都有可能被剧烈摇晃的军舰夹死。
大金门、小金门、大旦、二旦、马祖、北竿、南竿、东莒、西莒我全去过,甚至连很少人踏上的乌坵也到过。我们的小艇队在金门驻守过一年,晚上站岗时得非常小心地提防,以免被从对岸摸上来的“水鬼”给割了喉咙。可是在白天,透过望远镜就可清楚看到对岸跟我们长得差不多的哨兵。彼此虽然身处不同的土地,周遭的大海却是相连的,拍岸的浪花来自同一片汪洋。
快退伍时,当时的台湾“国防部长”蒋经国先生下令精简军队。我们的小艇队被解散,队员被分派至其他各单位,我也被调去了一艘运补舰。上了那条船,我的工作变得轻松多了,不必再背重得半死的PR77,而是守在舰桥上打灯号、升信号旗。
运补舰天天在各个小岛之间来来回回,最让我难忘的就是到乌坵的那趟任务。说实在的,乌坵岛小到只能算是一块大石头,但因位处海防要地,一直有军队驻防。那一回,船上除了依例载满换防的士兵、大量淡水以及各项补充物资外,还有一位通常在军舰上不大可能出现的女人。
原来,这位特殊的乘客因为非法卖淫被判了刑,在刑期内如果自愿前往外岛为士兵们服务,就可以不必坐牢。当时,军中为了解决外岛士兵的性需求,设有被弟兄们昵称为“八三一”的军中乐园,因为那儿的电话号码是八三一。在金门的“八三一”女服务员不少,在乌坵却只有一位,那天的那位乘客是去替换的。
由于身份特殊,那位三十来岁的妇人被安置在舰上一个不会受到打扰的空间,也就是我平时打旗号所站的瞭望台。在两三天的航程中,我偶尔会跟她聊聊天,得知她有一个好吃懒做的丈夫,三个仍在读书的小孩。所有的家计都落在她身上,为了要让孩子们有安定的生活、完整的教育,她选择了出卖肉体的行业。在言谈之中,她没有怨天尤人,只说为了儿女的前途,一切苦都可以忍受。
军舰在惊涛骇浪中靠近乌坵岛,岛上热烈的欢呼声盖过浪涛的怒吼。阿兵哥们蜂拥而至,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粗重的水管扛上军舰,在水阀上锁好,把水龙头打开。巨大的水柱洒向那群乐不可支的人;趁着淡水接往水塔之前,他们要好好享受一下天降甘霖的滋味。那位沉默的“八三一”服务员拎着简单的行囊走下舷梯,坚毅地步向办点交手续的军官。她的背影看来笃定而自在,仿佛确知,所有的罪孽都将会在一次一次的承受中洗净。
退伍后,我很幸运地进入《汉声ECHO》杂志。这是台湾第一本以照片为主要插图的刊物,以有系统地整理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为己任。在这里工作,除了让我开始拍照,还让我有机会在工作时吸取华夏文化的养分。在当时,《汉声ECHO》还只出英文版,这开启了我的眼界,激励我在日后创办《摄影家PhotographersInternational》杂志时采用中英文对照的方式,向全世界发声。
环境愈封闭,就会愈让人想挣脱局限。或许这就是岛民的特性,要挣脱的力道是这么大,以至于在不知不觉中,将范围拓展到超出自己原来的期望。每个岛民是否都拥有这般特性?而拥有这般特性,是否就能摆脱宿命?这就跟因缘有关了。时空不对,一切都会改观。
我时常觉得,我们这一代的台湾人真是最幸运的。日据时代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我们还没出生;国民党政府来台后,我们才呱呱落地,免去了所有的战乱经验。在所谓的白色恐怖年代,我们还小,整天只知道玩。稍稍懂事后,只要不涉及政治,爱怎么作怪,想如何前卫、反叛,人家也懒得搭理。等我们能发挥所学时,台湾的经济环境也好了,处处找得到舞台。
台湾这个岛屿,说小是小,说大也很大,因为它汇集了整个大中华的精髓。从农业社会跨向商业社会,再踏入信息时代,人类上千年的进化缩影,我们这一代的台湾人都沾了边儿。等到计算机盛行的虚拟时代来临,饱受传统文化滋养的我们已经茁壮得能够稳稳地挺住,有能力拒绝不良影响。在安定、没有巨变的环境中,我们得以坚守传统信念以及它的珍贵价值。
最令人感到欣慰与兴奋的就是,我们这一代还等到了两岸的友好往来。在ECFA(《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》)签订后,台湾与大陆将共创光辉荣景。原来的同胞曾一度成为敌人,六十年后的现在,彼此的兄弟之情终于又被唤回了。尽管在这新的一年,此岸的华人欢庆“民国”百岁,彼岸的华人纪念辛亥革命百年。
最近整理三十多年来所拍的照片,不只让我看到,也让我听到那环绕整座岛屿、袅绕几个世代,活力无限、韧性十足的浪花拍岸声。这些浪花被锁在尘封已久的抽屉里,将抽屉一一打开,童年的阳光、海风、咸味扑面而来。过去与现在又接续上了。
作者简介|阮义忠,摄影家、阮义忠摄影人文奖创始人。著有《失落的优雅》《二十位人性见证者:当代摄影大师》等。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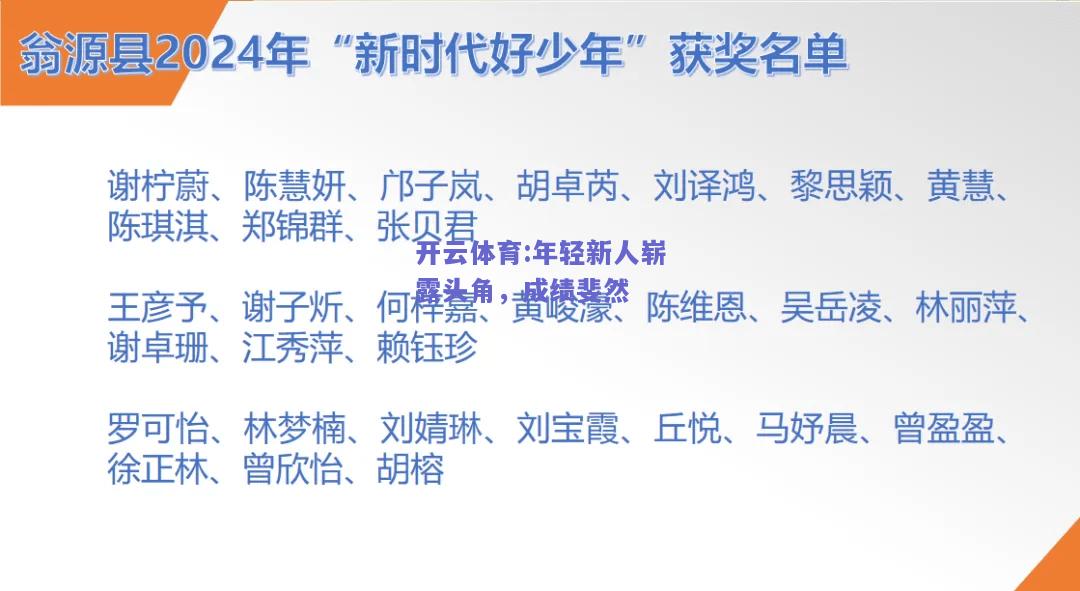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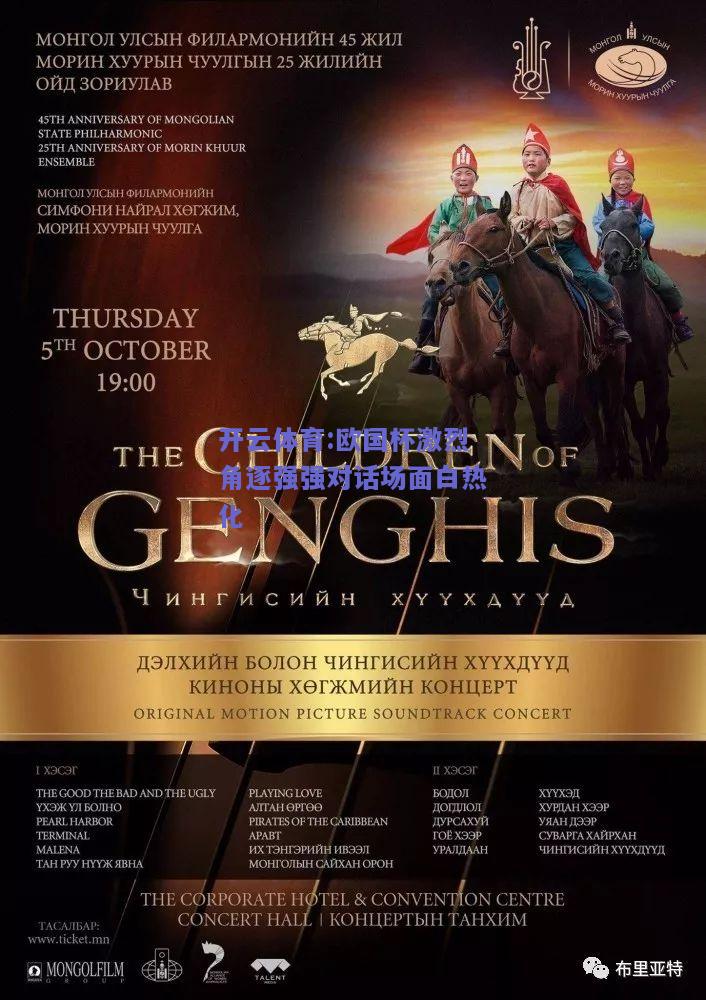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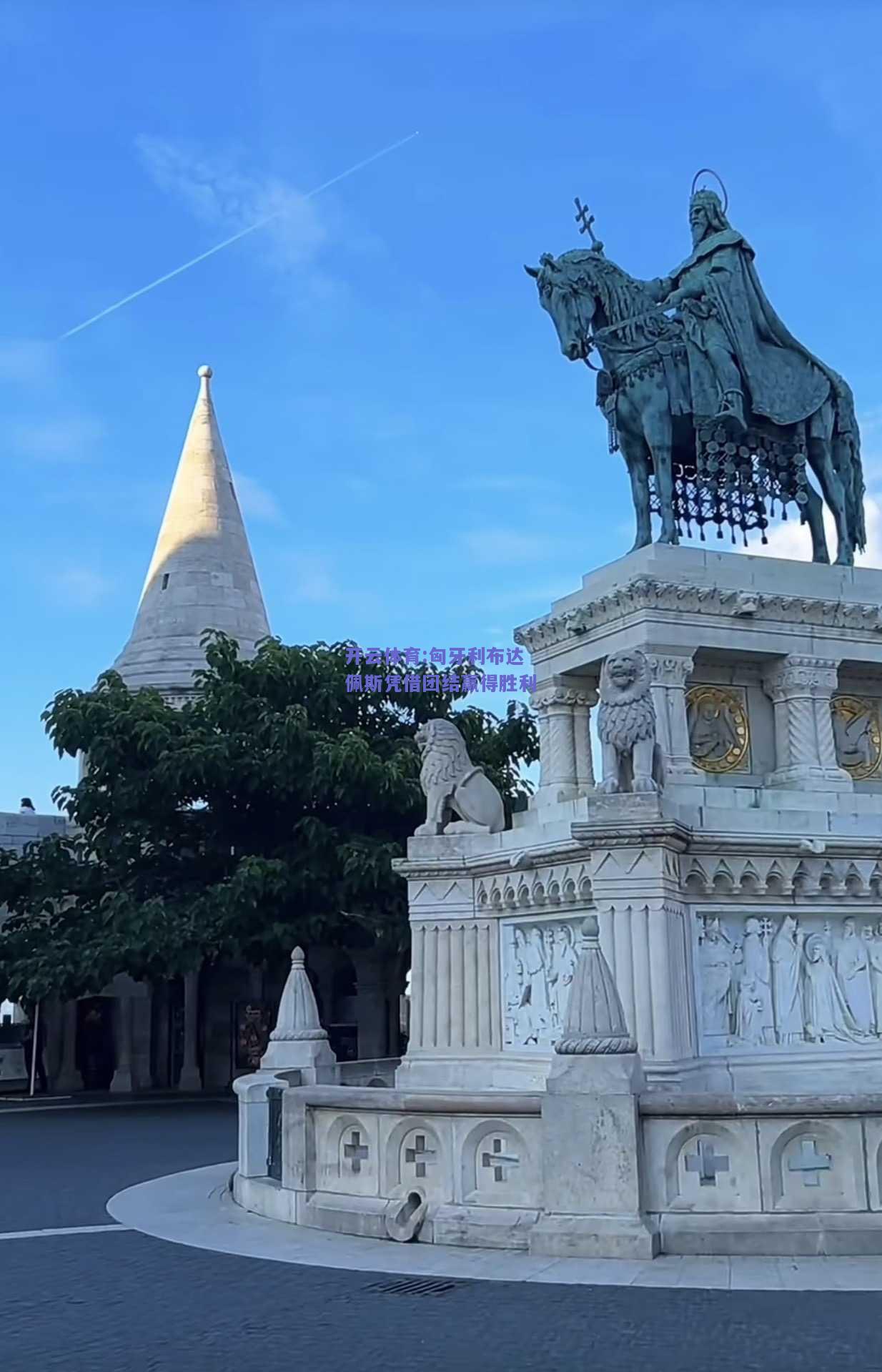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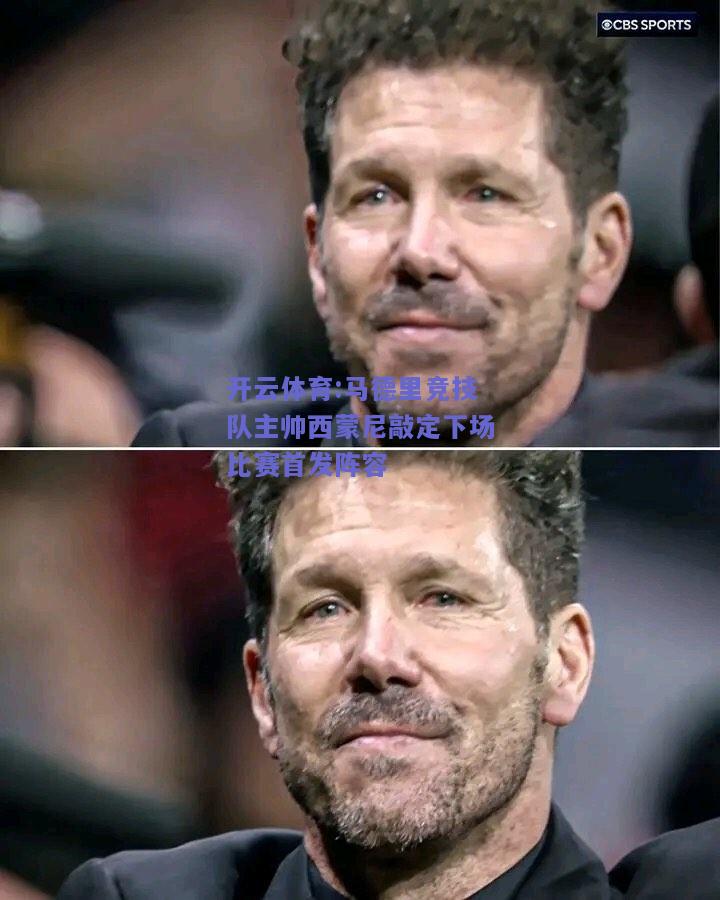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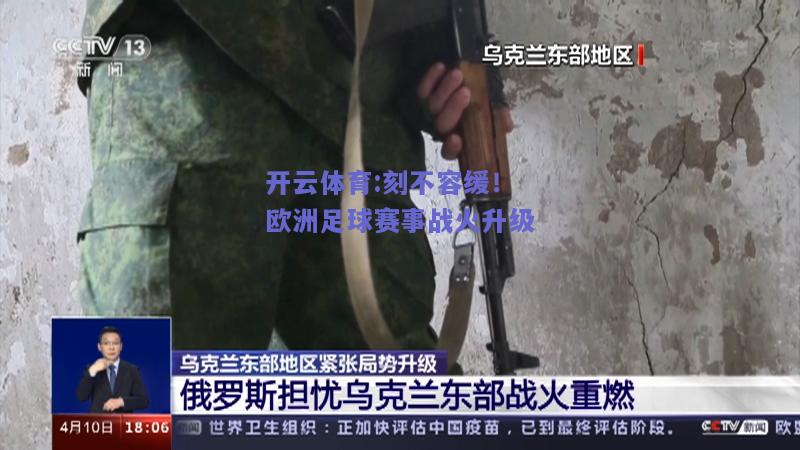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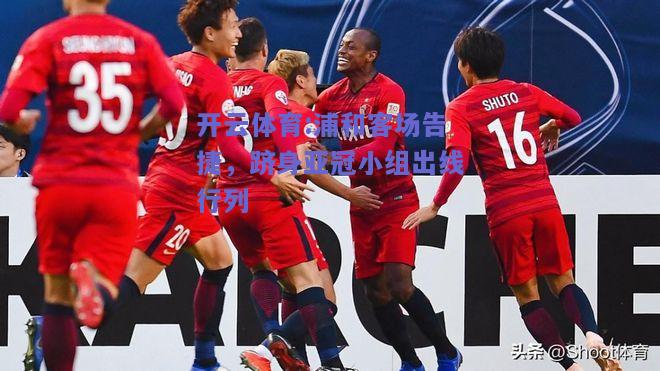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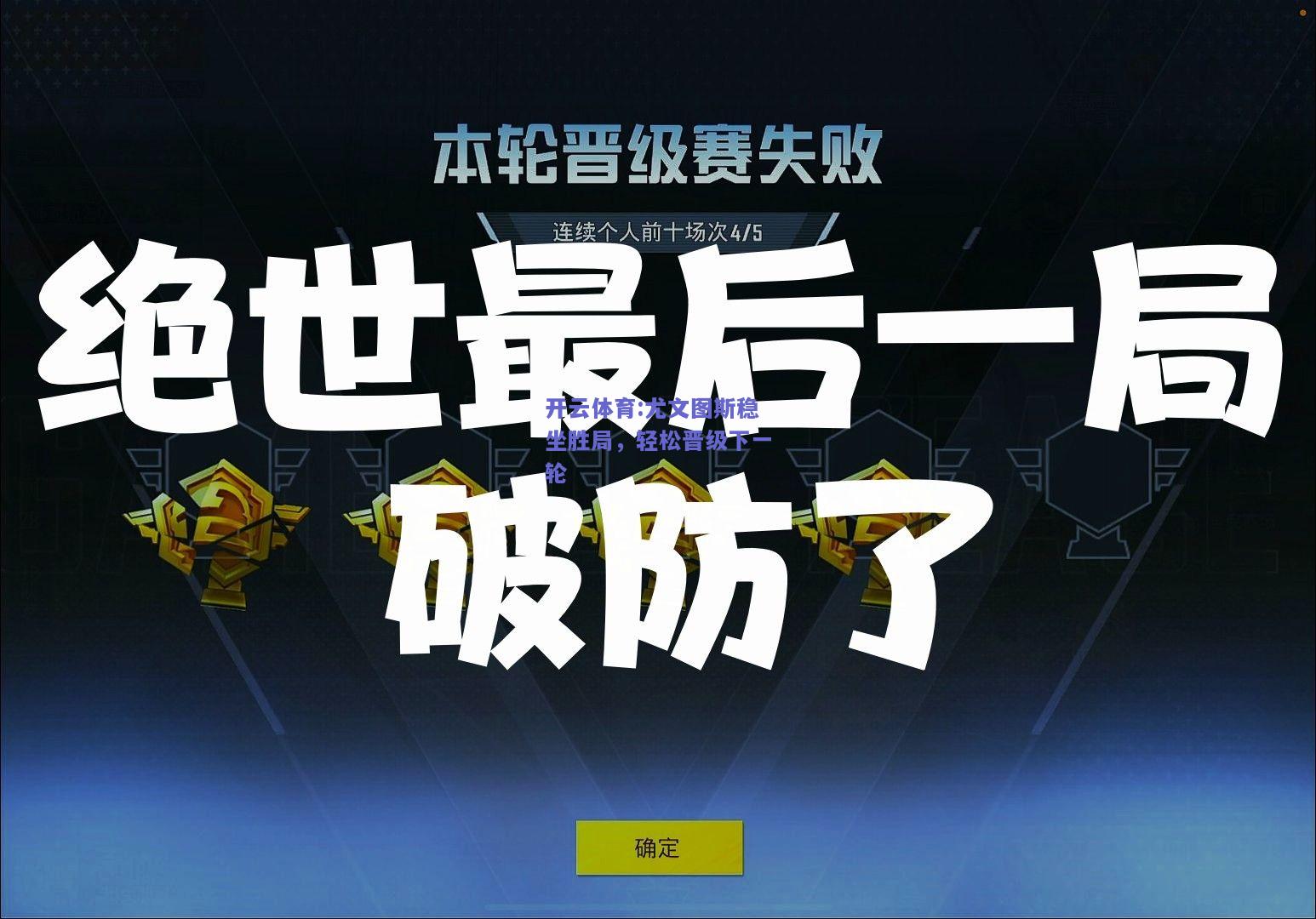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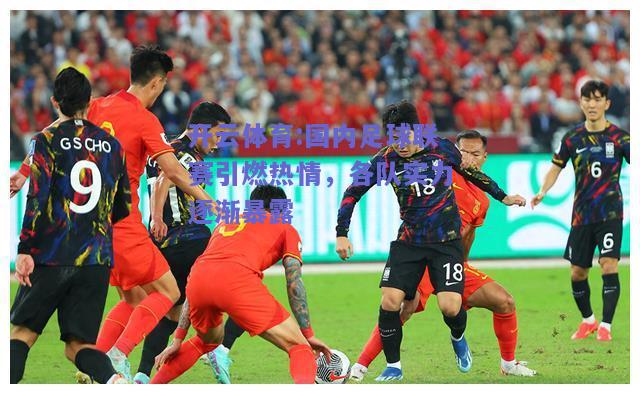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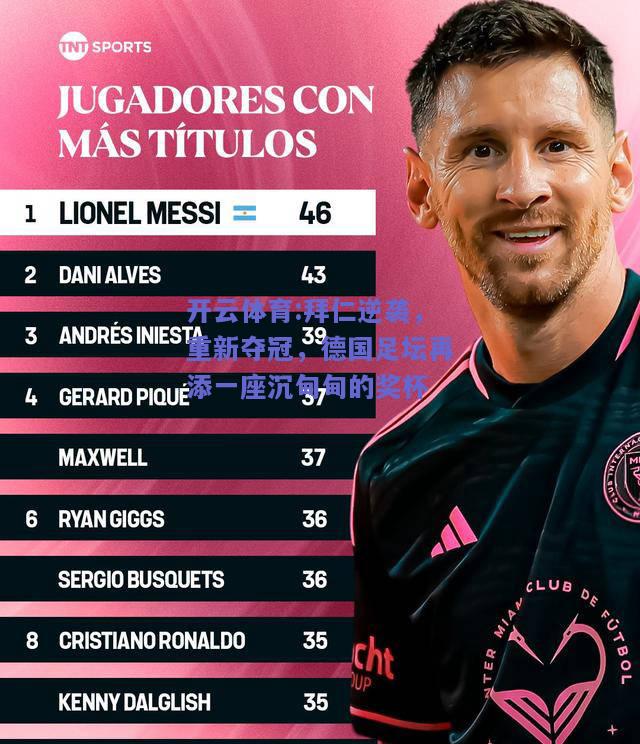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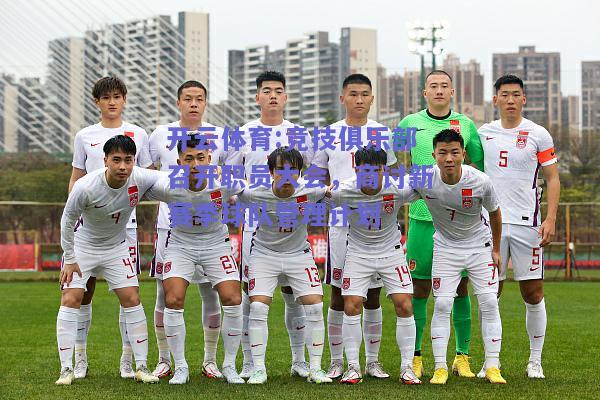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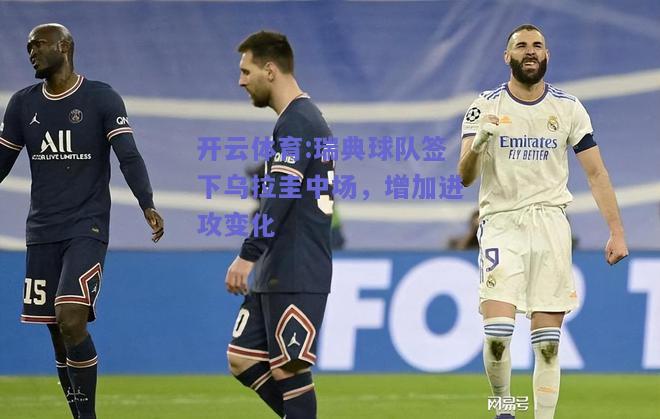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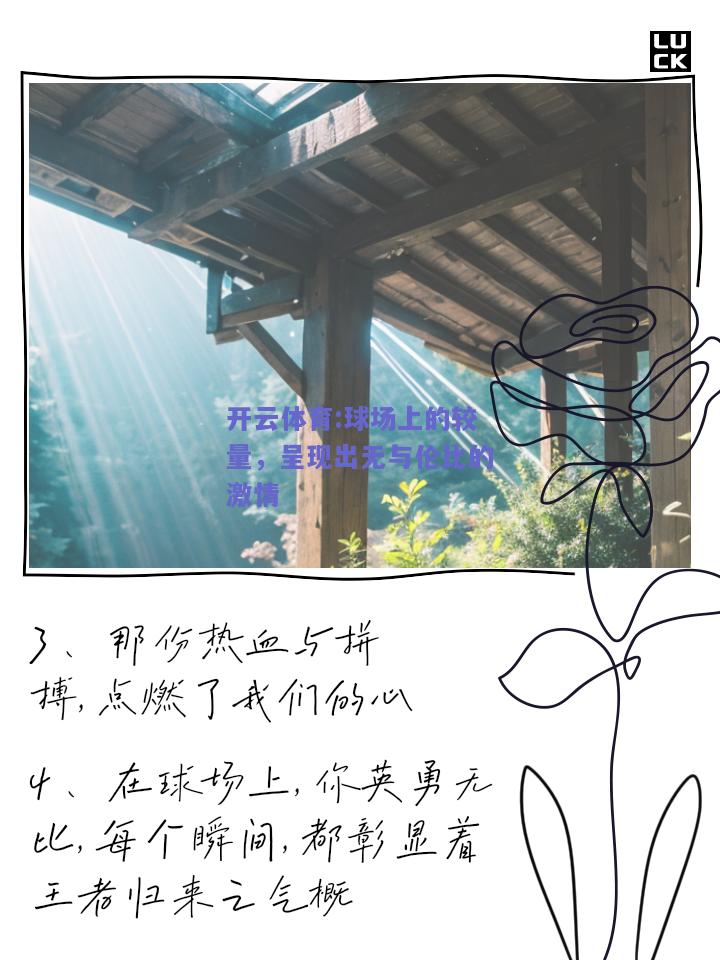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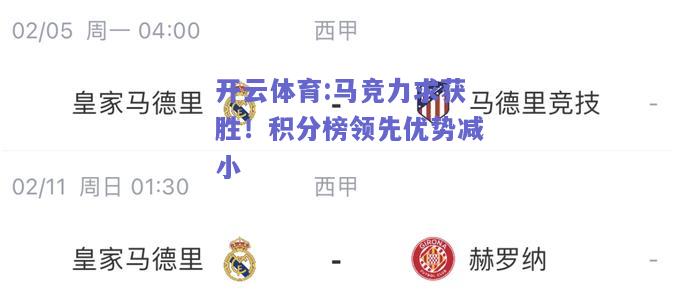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网友评论
最新评论